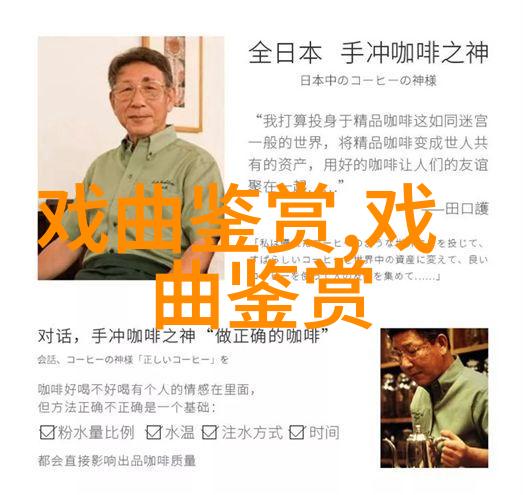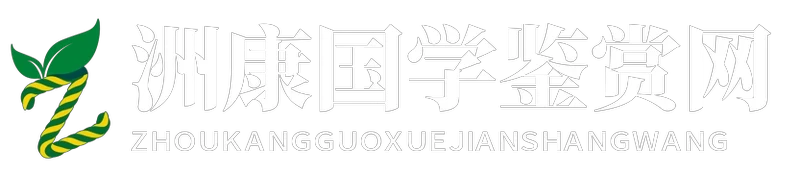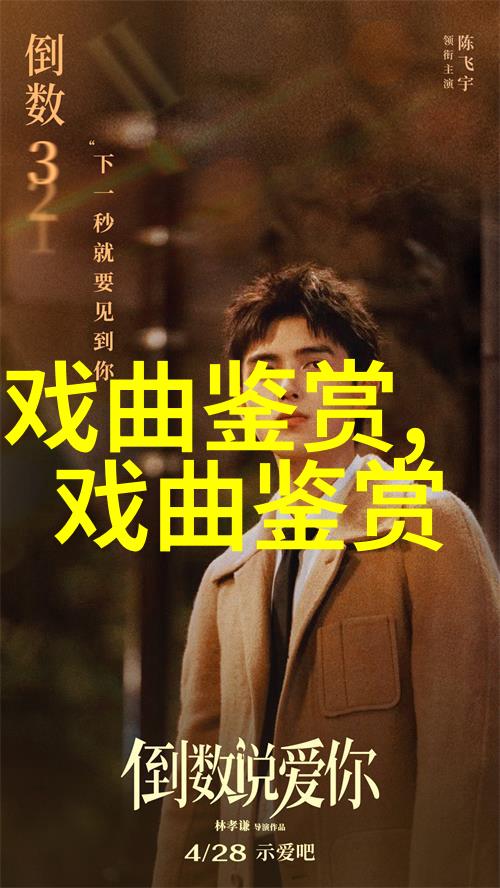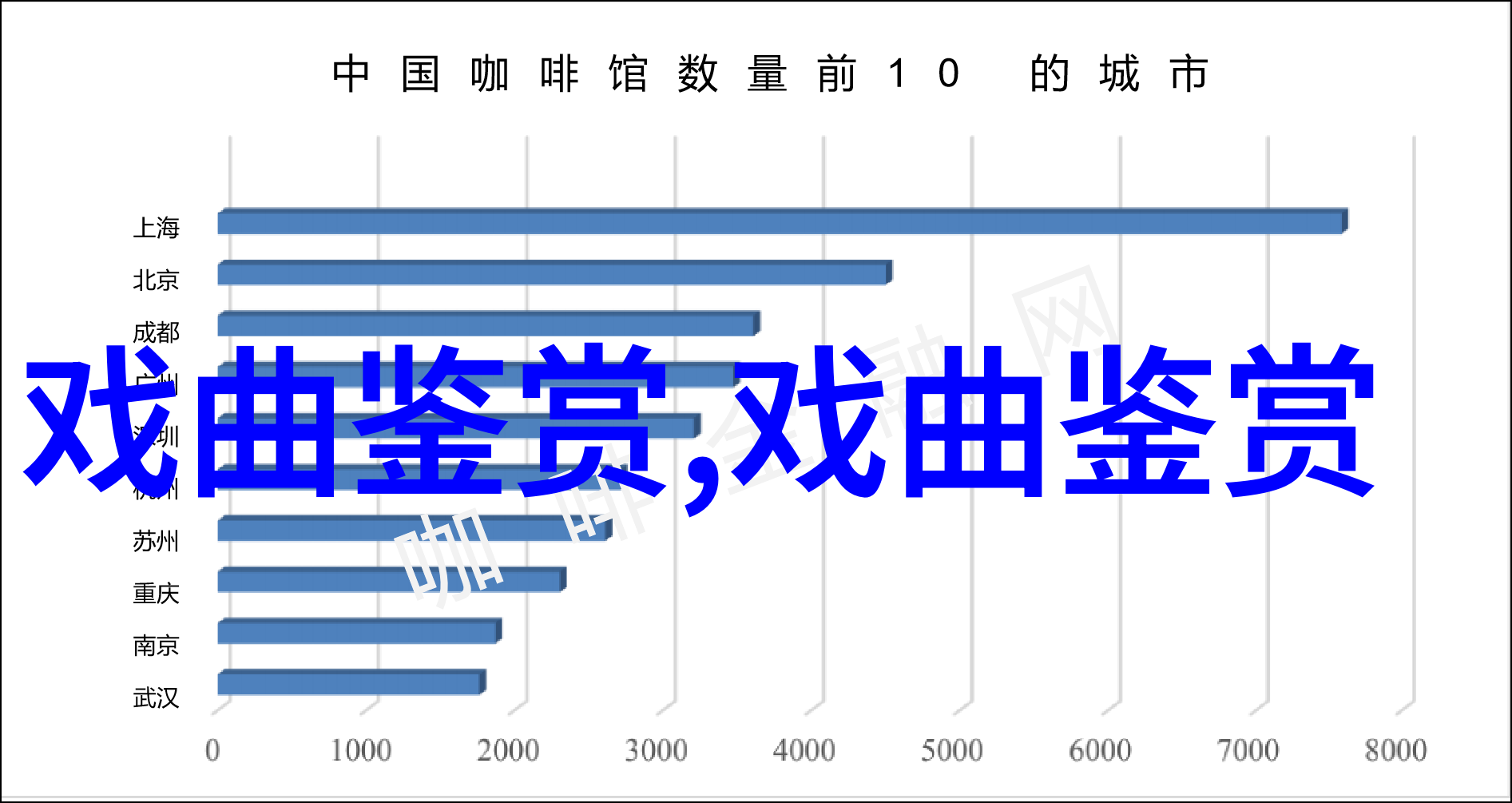有似公路电影的玉堂春
有似“公路电影”的《玉堂春》 那些经过时光淘洗的经典剧目,让人百看不厌。春节前后,在各大剧院推出的演出中,这些精彩大戏也是当仁不让的主角。从戏曲传承的角度来看,这些经典剧目不仅艺术水平高,还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,确确实实是教学的好教材。 京剧《玉堂春》就是其中之一。最近一段时间,北京京剧院、山东省京剧院、湖北省京剧院、济南市京剧院等,都演出过全本《玉堂春》或经典选段。国家京剧院陆续推出“这里有戏”系列专场演出,其中“琪树初长成”优秀青衣演员刘琪折子戏专场,将于3月4日晚在梅兰芳大剧院小剧场举行,这一专场包括《挡马》和《玉堂春》两台戏。在《玉堂春》中,刘琪饰演苏三。值得戏迷关注的是,国家京剧院特别注明,这台戏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老师亲授,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陈淑芳担任艺术指导。这更是让人充满期待。 《玉堂春》故事好看,戏好听,因此演员喜欢演,观众愿意看。很多观众都会唱“苏三离了洪洞县,将身来在大街前”。谁要是上了别人的当,受了些委屈,也常把剧中苏三的那句唱词“洪洞县里没好人”,用来当作调侃之词。 《玉堂春》的故事,见于明代冯梦龙著作《警世通言》中的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。小说中的情节是:明正德年间,苏三即玉堂春,因家贫从小被卖进烟花院。她才貌出众,成为鸨儿的摇钱树。礼部尚书的三子王景隆,与苏三院中相会,才子佳人,互相倾慕,继而海誓山盟,私定终身。王景隆钱财用尽,被鸨儿赶出院门,不得已暂至关王庙栖身。苏三得知消息,以进香为名,赴庙赠金,同时又嘱他努力考取功名,以待将来相见。王景隆还乡刻苦攻读,科场高中。另一边,苏三被卖与山西贩马的富商沈洪为妾。沈洪原配皮氏,私通赵监生,二人合谋欲害死沈洪、苏三。皮氏将辣面掺入砒霜,沈洪吃后丧命。皮氏趁机诬告苏三毒杀亲夫。县官受贿,将苏三问成死罪,并解至太原三堂会审。王景隆巡按山西,知犯妇即为苏三,决定先调审此案,在藩司潘必正、臬司刘秉义的帮助下,冤案昭雪。最终,王、苏团圆,皆大欢喜。 认证为百度2021百大创作者的著名文史博主浩然文史曾专门撰文介绍过《玉堂春》。这篇文章中介绍,冯梦龙所写的小说多来源于现实,且有后人考证,不管是苏三还是王景隆,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。王景隆的原型叫王三善,万历二十九年进士,今河南永城县人,在天启年间平叛土司时战死,谥号忠烈。1957年,田汉先生与山东大学《文史哲》杂志组成了一个团队,专门对《玉堂春》中的其人其地展开实地调查,根据三个方面理由,基本认定了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。文章总结说:“而且耐人寻味的是,永城王氏后人认为迎娶青楼女子是一件有辱门风的事情,所以他们对王三善和苏三的关系也是讳莫如深,甚至都不允许《玉堂春》在永城县弹唱,这也从侧面证明,《玉堂春》的故事或许就是发生在这里,而相对应的王景隆就是历史上的王三善。” 京剧中的情节,与小说大致相同,但也有一些改变。例如,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王景隆,是礼部尚书之子,但到了京剧中,王景隆变成了王金龙,其父亲的身份也变成了吏部尚书。那位山西马贩子,名字也由沈洪变成了沈燕林。另外,小说中介绍苏三时说,她“排行三姐,号玉堂春,有十二分颜色”,可知苏三早已有玉堂春的名号;在戏里,则是“玉堂春本是公子他起名”,可知乃王金龙来到春院后,方才为苏三取名玉堂春。 无论人名前后怎么变化,也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,《玉堂春》能流传这么广,且能久演不衰,魅力何在,又到底是哪些地方抓住了人心? 首先还是故事好。整个故事之委婉曲折,人物的悲欢离合,描述细致,丝丝入扣,又铺垫周密,合情合理,让人不知不觉地就能沉浸到故事中,所谓自然而然就入戏了。 人物刻画得好。苏三虽然身陷春院,但她是一位重情重义、有才有貌、有见识有智慧的奇女子。她出身不幸,流落烟花,而这件事非她能自主,更非她自愿。在她能自主的事情上,则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智慧与气度。她重情,对王公子一往情深,在王公子落魄时,依然痴情不改,并周全计划,私会赠金;同时,还勉励公子回乡潜心攻读,以求取功名。一个女子,如此重情义,如此守承诺,处事如此聪明,见识如此高远,怎不令人敬佩?观众看了又怎会不喜欢? 主题立得正。《玉堂春》该批判的批判,该褒扬的褒扬,善则扬,恶则贬。比如,贩马的富商沈燕林,贪恋苏三美貌,又自恃财产殷富,遂阴谋串联,瞒天过海,骗得美人归,旋即因此意外命丧黄泉。这样的情节安排,岂不是对这种恶行最有力的鞭挞和批判? 在主人公王金龙的形象塑造方面,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。剧中,对王金龙重情的一面,对他并未“始乱终弃”,是赞赏的;对他“浪子回头”后的矢志发奋、闭门苦读,最终科场高中,是赞赏的;同时,对他流连春院、挥金如土的行为,显然又是贬斥的。这种贬斥,通过不同的情节设计来体现。 最浓墨重彩的一段,当数“三堂会审”。此时,担任主审官的王金龙并未和苏三相认;参加会审的藩司潘必正、臬司刘秉义尚不知晓王、苏二人的过往。于是,潘、刘二人审案时,要求苏三先把自己的故事从头讲来。苏三自然而然地就要讲起与王公子的种种往事。潘、刘二人一唱一和,详加点评,当骂则骂。王金龙只能继续佯装不知,尴尬以对。 比如,苏三唱道:“初见面纹银三百两,吃一杯香茶就动身。”潘、刘两位大人闻听,不禁大吃一惊。三百两银子,还只是见面礼,这王公子出手可真是阔绰。即使在今天,有人算过,如果以大米为衡量单位,可以推算出,明代中期一两银子约相当于现在600-800元的购买力。按这个比例换算一下,三百两银子也确确实实算得上是一笔巨款。所以,潘必正感叹:“此公子可算慷慨得紧哪!”王金龙赶紧附和:“嗯,倒也大方。”刘秉义则说:“两位大人,说什么慷慨,讲什么大方,分明是他王门中不幸,出了这样败家之子。”明知道骂的是自己,可又无法反驳和辩解,王金龙有口难言,如坐针毡。最终,他只好以旧病复发为由退出庭审,由潘、刘二位大人代审。 “三堂会审”这一场戏,记者感觉特别像看一部“公路电影”。苏三的一段经历,随着时间线徐徐展开,那旧日情境一一重现。碍于种种原因,王金龙不敢与苏三相认。潘、刘两位大人先是被蒙在鼓里,后看出端倪,他们心照不宣,有心戏弄一番巡按王大人。四人之间这种有趣的关系,把故事性、戏剧性拉满。同时,这种设计,在故事一步步推进的过程中,在谜底一点点揭开的过程中,又巧妙完成了对王金龙流连春院行为的毫不留情的批判,从而使主题始终立得正,立得稳。 这样的《玉堂春》,演员常演常新,戏迷常看常新。这也正是这些经典老戏的魅力。 前不久,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傅谨教授在《中国文艺评论》发表文章,系统评述2022年度中国戏曲,其中再次谈到戏曲的传承与传播问题。在传承方面,他特别提醒,戏曲危机并非缘于“老戏老演,老演老戏”,而恰恰是高水平的传统经典难得一见。 傅谨分析认为,多年来,人们认为戏曲境况不佳的主要原因,是戏曲行业在传统面前故步自封、缺少创新能力与意愿,努力推动创作新剧目才能让观众回到剧场,所以各地的戏剧节和艺术节无不侧重于新剧目的展演与评奖,但从实际效果看,实有南辕北辙之嫌。普通观众对新剧目的追求是商业剧场时代的普遍现象,传统戏过于频繁出现难免让其厌倦。但是新剧目因未经时间淘洗,质量必然参差不齐,就平均水平而言,在经历千锤百炼的传统戏面前缺乏可比性,舍弃传统经典必然导致该艺术门类的整体水平下降。 他说:“戏曲乃至所有艺术门类,当然需要在传统基础上不断有新作品的加入才能构成其发展的主线,然而缺少传统经典的支撑,演出市场既失去了最优质的文化产品,也失去了最忠实的观众;而对传统及其价值的轻视,决定了新剧目难有真正高质量的创造性表达。” 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,像《玉堂春》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出,不仅能够有力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传播,也能够为戏曲创新找到新的打开方式并提供坚实的力量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