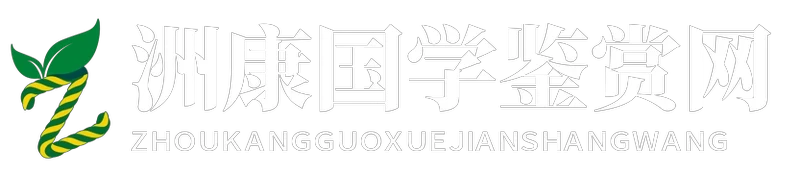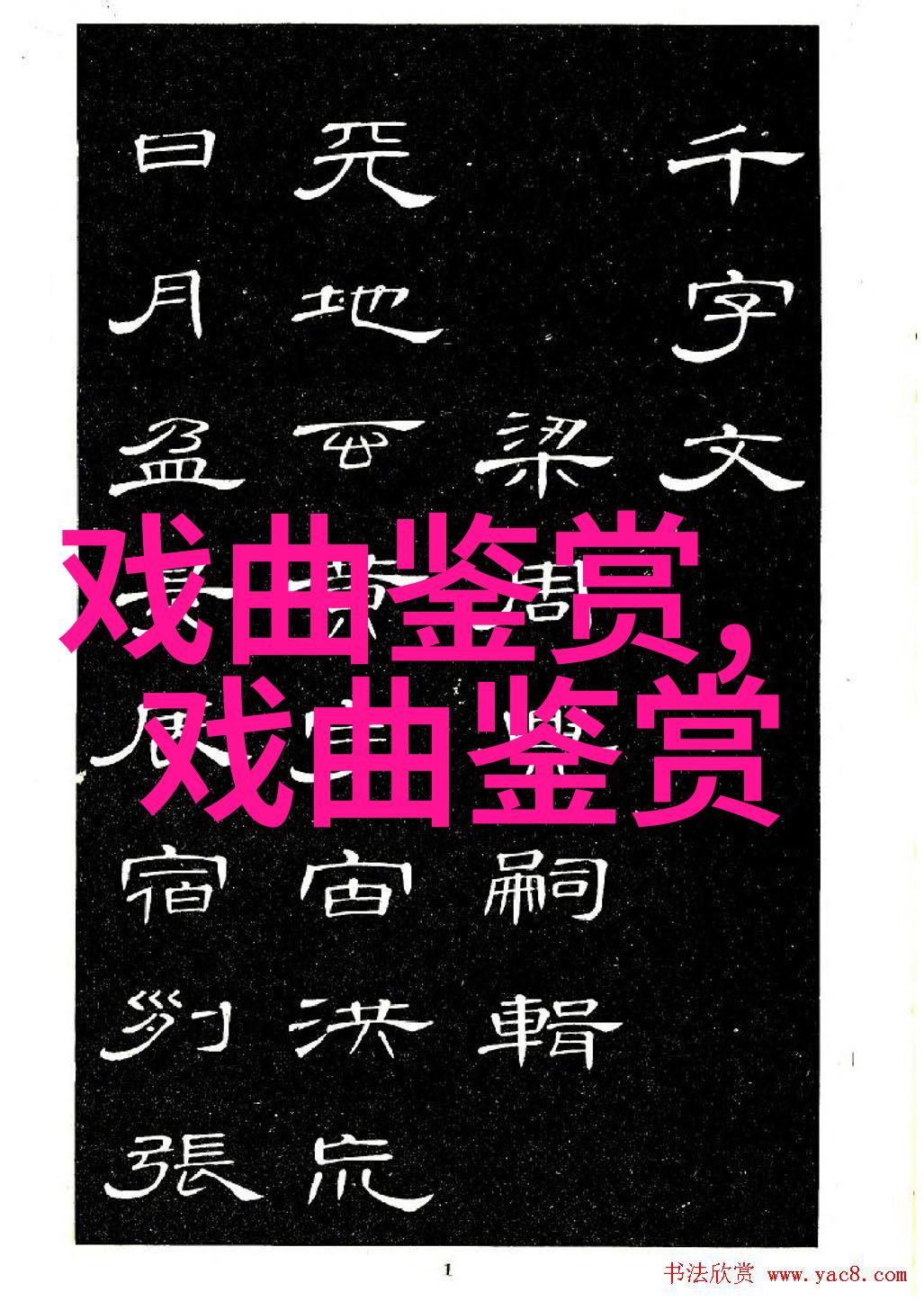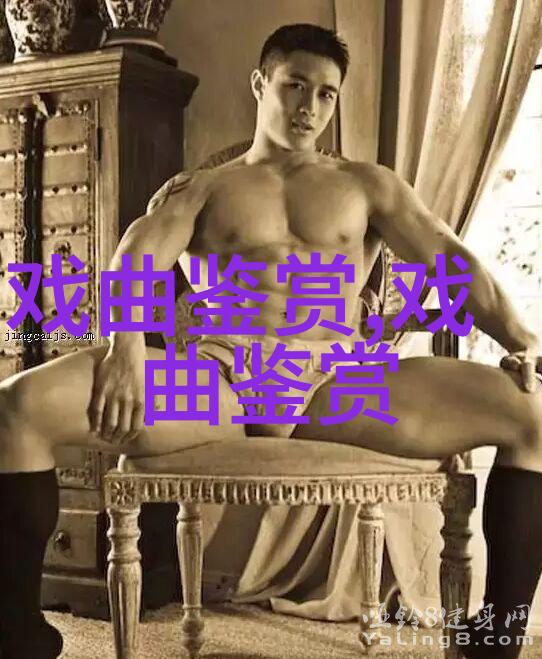给跨流派京剧表演更多宽容
评论 给跨流派京剧表演更多宽容 8月31日,梅派青衣史依弘在京上演程派名作《锁麟囊》,场面火爆,跨流派京剧表演这一现象也再度为人们所关注。 所谓跨流派演出,有的是以本流派方式演绎他流派剧目,如程派名家张火丁演出梅派经典《霸王别姬》;有的是以他流派方式演绎相应流派的剧目,如宗梅派的史依弘在演出《锁麟囊》时,从声腔到表演都向程派靠拢。跨流派演出面临着“不务正业”等指责,但笔者以为,对于跨流派京剧表演无需剑拔弩张,不妨多予宽容、共谋发展。 京剧艺术拥有众多流派,这是其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。流派在基本程式之外,为演员提供了一套现成的、独具个性的表演方法,一种看待人物、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。与前者相比,后者构成了不同流派之间的本质性差异,只是这一点在十分强调技术、“玩意儿”的京剧界鲜少被讨论。如果说,出身京剧世家的梅兰芳艺术之路顺风顺水,身边有“梅党”的多方助益,他对世界、人生的感知投射于艺术,形成雍容华贵、平和优雅、大气自然的梅派风格;那么,“落魄贵族”出身的程砚秋经历幼年困顿、少年倒仓、恩师去世等磋磨,人生几番起落,幽咽婉转、钢锋内敛、绵里藏针的程腔中何尝不浸润着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呢?试图垄断生命与情感体验的各种尝试终将徒劳,它作为无比接近艺术本质的东西,不断呼唤有才华的艺术家去投入、挖掘、表达,艺术的天地因此而愈发丰富充盈。对于成熟的演员来讲,在生命、情感、世界观层面上体悟流派后,再去学唱腔、身段,并不是一件困难、危险到必须禁止的事。 倘若逻辑的推演有凌空蹈虚之感,那么便不妨从历史中寻求宽容对待跨流派表演的扎实素材。京剧流派是历史的产物,为不同时期的观众提供着多种多样的审美选择。流派在时代社会的发展、审美观念的更迭以及艺术与观众的互动中传承、创新,并非铁板一块。从形成历史来看,几乎每一个流派都是在博采众长、兼容并蓄中开创的。譬如创立旦行张派的张君秋,其《牧羊卷》得程砚秋亲传,张派声腔中的梅派痕迹也不难发觉,而梅兰芳、程砚秋作为不同流派的开创者,又有着共同的老师王瑶卿,师门的复杂渊源以及艺术上的切磋交流,并非一句“这是某派、那是某派”就能完全切割。再如,奚啸伯票友出身,以天资、学识与勤奋跻身“后四大须生”并开创奚派,其声腔、表演中依稀可见谭、言、余、马等众多老生流派的踪影。就剧目角度而言,许多骨子老戏本为各流派所共享,经艺术家加工提升后而成为流派代表作,梅兰芳之于《贵妃醉酒》便是如此。历史事实是,即便《贵妃醉酒》成为梅派代表作,旦行其他流派演员也仍在演出该剧,相关录音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。相较于骨子老戏,由流派创始人及其团队原创的剧目,跨流派演绎起来自然困难大些,但也实无必要将这种流转可能性扼杀、在流派之间划定不可穿越的红线。 放眼历史,流派创始人都是极具包容精神、创新精神与开拓精神的艺术大家,京剧之传承不仅在于技术、作品,更在于格局、气度、境界,倘若太过于固执、保守、刻板,首先就在精神上背离了前辈。过分追求所谓的“纯粹”绝非捍卫流派、捍卫艺术,而是暴露了偏执与狭隘,抑或生怕别人动了自己那块小蛋糕的风声鹤唳。 随着时代发展,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流日益深入、频繁,不少艺术形式积极向戏曲尤其是京剧学习借鉴,比如话剧《祖传秘方》、歌剧《画皮》、音乐剧《京·谣》等,近年来,京剧元素也不断出现在影视剧中,成为重要看点,提升作品的美学格调。然而,京剧乃至戏曲主动向其他艺术形式借鉴的例子,有多少呢?海纳百川有容乃大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,还是值得好好揣摩。 不论梅尚程荀,还是马张谭裘,大家共同的名字是京剧人。呼吁给予跨流派京剧表演以更多宽容,其实也是呼吁给创新开拓精神以更多宽容、给博采众长的艺术实践以更大动力,更是给京剧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以更广天地。